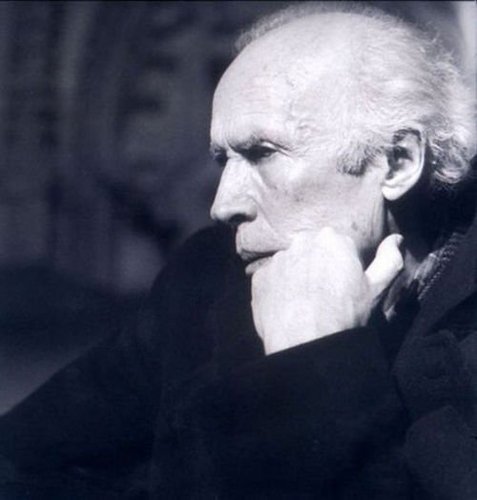
法国著名导演侯麦。(资料图)
一、用不变对抗潮流
作为法国新浪潮的旗帜人物之一,埃里克•侯麦是难以形容的。他的画面不具有颠覆性的冲击力,题材也不具备夺人眼球的政治敏感性,剧情更算不上充满悬念引人入胜,他的作品缓慢、优雅、细腻,但绝不是那种一味追求唯美的形式化影片,他用人物连绵不断的语言与思辨,勾画出电影中少有的文学性。他让很多似乎并不适合拍成电影的剧本,成功地搬上了银幕。当大多数导演都在追求创新变化时,尤其是《电影手册》中一些青年人激进地批评他的电影保守时,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电影理念,对抗潮流。可以用其作品《午后之爱》中的一段台词,来解释他对于电影与时代潮流,或者说理想之于现实的冲击:“我爱大海,不是为了将自己吞没,将自己融化,而是在它的表面航行,循着海面的节奏,静静地破浪而行,以便找回我自己的节奏。”对于曾经在教育电视台担任工作的侯麦来说,首先是名作家,其次才是电影人,但并非就可以认为电影只是他传达小说意愿的一种手段,他总是说剧本的内容,用电影拍出来,又是另一个故事,另一种味道,摄像机有它自己的语言和讲述方式。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许多新浪潮导演都拍摄出了自己的代表作,侯麦也继1959年的长篇处女作《狮子星座》之后,在1962年到1972年拍摄出了奠定他影坛地位的“道德故事”系列。很少有导演像侯麦这样喜欢拍摄系列,而且系列中的每部作品都是在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乐此不疲。“道德故事”系列的主题是建构在这样的一个构想上的:“一个男子想和某个女子结交的同时,他受到了另一个女子的挑逗。”其中心人物可以是各种不同性格和状态的,比如《苏珊的生涯》中腼腆青涩的贝尔朗特,《女收藏家》中热情自由的阿德里安,又或者是《幕德家的一夜》中恪守清规戒律的工程师。侯麦借此尽量从有限的主题中发展出更多的可能。一些不喜欢他的评论者认为,他没有创造出什么全新的东西,对此,侯麦自觉自己更像是音乐家,把有限的一些音符,重新组合,谱出动听旋律。而系列中的各个影片,就像是同一主题下的变奏曲。对于为何他如此喜欢总是探讨一个主题,侯麦的解释是,这种方式比较容易传达出他的“意念”,不去关心观众喜欢的题材,而是劝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同一种题材拍六次,但愿六次以后,观众就领会其意。
二、移动的风景,永远的巴黎
“道德系列”的第一部《蒙索的女面包师》虽然片长只有23分钟,却奠定了整个系列的风格基础。前几个镜头都在描绘巴黎的景观,维利尔大街,笔直交错的街道,街角的咖啡馆,地铁站,延伸到街道尽头的蒙索公园。而全片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巴黎的大街上,皮埃尔邂逅心仪的女孩,游荡在大街上想要和她见面,来往于面包店与学校之间。巴黎始终是影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充分衬托出人物内心的百无聊赖和不同的情感。每次遇到希尔维都是在开阔的大街上,车辆传流熙攘,阳光充足,舒展而自在的空间,让人感到男主角内心的坦然。而位于勒波特大街上的面包店,被多栋楼房挤在街角,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连光线都不能直接投射进来,暗示着一段见不得人的情感在皮埃尔心中的滋生。他就在这里引诱喜欢他的面包店女孩杰克琳。
人物所处空间的转换在侯麦的电影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同变幻的建筑物,四季风景,都是在导演精心挑选下呈现在银幕上的,也就与故事的戏剧性有着很强的关联。当然,有故事的永远不是风景和建筑物,而是在于处在其中的人物,还有他们对于这些风景的视角,以及导演如何将这些画面呈现给观众。如果仔细观察,除去地点的变化,对于环境的关注和调度始终是侯麦不变的特点之一。关注都市化情感一直都是侯麦几个系列中的特色,不管是“道德故事”系列,或是新浪潮之后的“喜剧与谚语”系列,还是九十年代的“四季的故事”系列,全都以都市人物的个人情感为主线。巴黎也一直是侯麦镜头所热爱的地方,它不断出现在侯麦的作品中,《苏珊的生涯》、《好姻缘》、《圆月映花都》、《冬天的故事》,巴黎那些近在咫尺的街道,总能制造各种邂逅与相遇的可能。在《苏珊的生涯》中,贝尔朗特一直想躲避苏珊,但也许巴黎太小,他总能被她逮个正着。巴黎又在《冬天的故事》中,再次成为让男女主角相遇的重要场所。而不同角色对于同一地点的不同感受,也都反映出他们性格的不同。比如在《克莱尔之膝》中,劳拉一家人住在阿纳西湖河畔,被群山环绕。劳拉的妈妈并不喜欢住在山脚下,她认为这样让人很不自在,山峦的雄壮让她窒息,感到威胁和压迫。而劳拉却觉得从室内看风景,很漂亮,就像身处摇篮之中,感到被保护的安全感。劳拉的母亲对男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所以让她处在过于雄伟的景色之中,处于地位较低的一面,她觉得受压抑。而劳拉虽然也对爱情有占有欲,但是她又有一种恋父情结,希望被年长的男性所保护,于是群山反而让她感到了安全。
侯麦还喜欢让影片中的人物,从一个居所移动到另一个居所。每个居所都对她代表着一定意义,都在展现他(她)情感的一面。“道德故事”系列中,都市总是代表一种诱惑,尤其在《午后之爱》中,弗里德里克喜欢漫步在巴黎,观赏女人,类似的镜头也出现在《蒙索的女面包师》和《苏珊的生涯》中,这些故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男性审视街头女郎的镜头。而在《女收藏师》就把场景搬到了外省的乡间别墅,在《秋天的故事》中,则干脆把大部分场景设置在葡萄园,都是一种对于都市的逃离,但他们终究与都市,与这些恼人的情感撇不清关系。在《春天的故事》中,让娜则有两个住所,一个是和男友的住所,一个是借给表妹居住的单间公寓,都不具有家庭的氛围,而另外一个就是娜塔莎的住所,虽然这里曾经是家庭活动的场所,但也只是一个名义上留存的符号,实际也并非一个完整的居所。这也隐隐构成了这部作品中,在繁花似锦的春天里,潜伏的种种冲突与矛盾,都并非一开始所看到的那么美好单纯。哪怕在侯麦晚期的作品,2003年的《三重间谍》中,对于场景变换其手法的运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给妻子调养身体,费奥多从巴黎搬到了郊区。场景也由封闭的公寓到了有着落地玻璃窗的别墅,虽然主人公仍旧在室内对话,但是窗外清晰可见的风景,让人感到私密受到了窥视,费奥多的间谍身份也由此一点点被暴露出来。
三、语言的艺术与时间的标签
对话一直是侯麦影片中最受关注的风格组成部分。但也被一些评论家批评为过度依赖对白。侯麦的理解是这样的,语言对电影和生命都很重要,和影像同等重要,对白显示了角色的内心,和动作、目光、眼神一样能传达信息。而所谓对话自然最少需要两个人进行交流,在影片中也能看到多个人坐在一起进行交谈。因为侯麦的主角大多是都市知识分子,艺术家,所以他们的对话也都经常涉及爱情、生活、艺术和哲学。这些对话大多是事前就精心写好的,只有《绿光》中的对话是即兴的。侯麦电影的对话风格一般是戏谑的宣言和一种挑衅,还有一些主角会说出类似警句的话语。比如《克莱尔之膝》中的男主人公就喜欢宣讲自己对于女人的看法。影片中的人物,一般都会有一些意见上相左的情况存在,比如《苏珊的生涯》中,羞涩的贝尔朗特和浪荡子纪尧姆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贝尔朗特总是看不惯纪尧姆的做法,却又说他们俩有相似之处。同样,这种反差,在两位女性身上也有,如《春天的故事》中的让娜和娜塔莎,但她们也同样有性格中相似的冲动与好强。用米歇尔•塞尔索的话来说,“对于侯麦的人物,一方总是另一方的镜子。”他们相似又对立,喜欢滔滔不绝地分析自己,又喜欢拉着对方加入其中,但是很多时候,当几乎达到共鸣时,又产生了分歧。于是他们的对话基本上就处于一种起伏的状态,擦出思辨的火花。这一点在他晚期的作品中也有保留,但是更加精减,也有所变化,在《三重间谍》中,对话更多的是充当了营造紧张气氛,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画外音的艺术一直也在侯麦的影片中具有一定分量。在他的一部分影片中,完全是依靠旁白完成了整部作品的叙事与思辨。在早期作品中,画外音往往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主人公本身。《蒙梭的面包店女孩》就用皮埃尔的旁白揭示了他所有内心矛盾的冲突,他的自恋与懦弱。到了《女收藏家》中,画外音虽然已经不是完全的主导,但是却和故事得到了更好的结合。在画面空白的时候,画外音是叙事性的,而当画外音出现在有人物出现的场景时,却往往是宣讲内心思想的。可以说画外音的艺术是侯麦在新浪潮时期的作品中最注重运用和发挥的。到了近年的两部作品《三重间谍》和《男神与女神的浪漫史》中,画外音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其作品中,那就是在影片结尾以一个局外人身份做一个叙事性的总结。
给时间贴上标签也是侯麦经常运用的拍摄手法。从“道德系列”的第一部,他就用广场的时钟来告知时间的存在。到了《克莱尔之膝》中,就变成了日期卡片式的手法,通过时间的跨度来观察男女主角思想上的变化。这个手法断断续续出现在侯麦各个时期的作品中,只是在时间单位上有所不同而已。
侯麦没有照搬新浪潮影片大多具有的风格和特点,而是从中汲取了符合他作品的特点,再将他的理念编织进去,形成一种全新的风格:现实主义、质朴、清新,但绝不粗糙,也不是即兴的创作,他有时甚至会提前一年去寻找电影中需要的植物和风景。而且侯麦的电影鲜少受到时代政治时局的影响,当时法国爆发了五月革命后,许多导演的创作风格都受到了影响,只有侯麦依旧拍摄了完全没有政治色彩的《穆德家的一夜》,依然故我的讲述都市知识分子的故事。当然,从每一部他的影片中,都能看到当时时代的一些思想特征。这也是为何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在有限的风格和主题中,还能让自己的作品不断焕发新的神采,这就像他说的那句话一样:“我从未能真正结束我的电影,因为结尾总会震荡出不同的方向,仿佛回音一般。”
[责任编辑:lilylin]
